AI时代的战争
- 资讯
- 2025-02-13 14:36:09
- 20

整整40年前,我曾短暂地在美国空军工作,研究一项技术,巴基斯坦空军正寻求为其新引进的f -16战斗机获得这项技术。在军事航空界,特别是在南亚,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补充。美国和以色列空军携带了一种变体,但其余的都是新-新。就在那时,通用动力公司(现在的洛克希德公司)开始宣传其针对F-16的“一弹一靶”战役。它的准确性是致命的。作为团队测试飞行能力的一部分,进行了大量的添加和改进,使其成为一个不干涉的自动瞄准系统,可以减轻飞行员的思想负担,现在可以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这和其他类似的奇特的增加了战士的能力带来了所谓的军事革命(RMA)。
后来,随着武器和平台在空中和地面的瞄准、跟踪和交战目标方面不断获得更高的保真度,杀伤力不断提高。与远程轰炸相关的类似能力是由武器实现的,这些武器在飞行中被控制时可以滑翔很长一段距离,直到它们到达最终阶段,以自主模式开始主动跟踪。直到1980年代早期,世界上最先进的空军都局限于使用中短程反辐射导弹来对付发射电磁辐射的目标——雷达的简称。1982年,以色列空军在贝卡谷地与叙利亚的短暂冲突中使用了这些武器,效果非常好。像F-16这样革命性的东西的发展和引进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思想和理论伴随着更新的思想和就业选择。随后发生的事情真正突破了门槛,引发了一场战争艺术的革命。
这就是F-16驾驶舱的运作方式:一项典型的任务是在与一群敌方战斗机和地面防御系统战斗的同时攻击地面目标。驾驶舱内脱口而出了警告、指示、目标解决方案和就业选择。飞行员手头有两项紧急任务,清理决策过程——确定优先级——并激活相关反应。它可能是在迫在眉睫的威胁下的紧急飞行机动,或激活干扰选项以破坏敌人的目标解决方案,启动自卫被动措施,并追求轰炸目标或消除空中对手的目标。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都是同时发生的行动,但关键是要把握好顺序和时机。除此之外,还需要在头脑中记住谁在哪里,朋友和敌人-情况意识-同时仍然指挥,控制和执行飞机编队的使用,以追求其目标。每个人都有宝贵的时间。可预测性可能致命。
飞行员获得的很多信息都是通过机载传感器或从编队成员和其他支援飞机那里听到的。许多年后,独立的人工智能使飞行员的工作量变得更容易,它根据预先输入的算法分解复合威胁,按优先顺序分配飞行员必须承担的任务。编队指挥官根据他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合成图像,将其他目标分配给其他成员,即使他正在进行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任务。在战斗机和支援飞机编队内以及与空中其他控制元件的即时通信和数据交换现在可以在每个驾驶舱的每个屏幕上生成合成的空中图像。飞行员分配他们的主要和次要搜索和目标区域,并通过数据交换共享彼此的信息。机载计算机已经连接了飞机系统、武器、传感器和自主激活的解决方案,减少了飞行员的工作量,使他有时间致力于最优地利用包裹中携带的全部破坏性能力。量子计算的早期模型以光速推断战斗机自己的参数,敌人的数据,并显示即时解决方案。过去的电缆和滑轮现在是通过每架飞机上的专用链路连接的数字传感器、发射器和接收器。人工智能副驾驶已经活跃了几十年。
正如在现代生活中,“物联网”(IOT)和“系统的系统”成为掌上和控制的生活方式管理系统的组成部分一样,战斗机飞行员在过去的40多年里确实生活在这些工具中。当时的流行词是“系统集成”。作为实验室的一员,创造和激活现代技术的这些过程,在当时确实是一种不太受重视的特权。随着计算速度的加快和这些计算机核心芯片的更多功能,战斗机将变得超快、超精确、超致命和超能力。战斗机将始终保持相关性,因为在人在环方程中,态势感知(SA)将是战斗中任何动态情况下最大的x因素。无人机是一种单任务机器,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完成目标,除非它在到达目标之前被吹走。就业选择将需要通过即时通信和计算将所有类型的能力交织在一起。
人工智能对战士的作用现在将超越战术发展到作战和战略。前提是训练机器模仿人类的反应。最高级别的战争决策与其说是基于既定情况,不如说是基于不断演变的战争性质。如果一台机器在长时间接触一个指挥官的决策偏好后,只学习了他的思想,它就有可能复制他的思想。但是,情况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指挥官和他们各自的思想也在变化——战争的艺术在应用和使用上可能在防御或进攻的程度上有明显的变化——这使得机器几乎不可能复制和学习到足够的行动,并在这些情况下自主决定正确的行动方针。模拟可以帮助机器学习,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所提供的东西永远无法与处于同一指挥水平的作战人员的智慧和决策艺术具有同样的可信度。
随着人类和机器在包括战争在内的大多数生活活动中融合,核武器的指挥和控制将成为阿喀琉斯之踵。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在任何程度上,都必须留给机器的突发奇想,不管这些机器最终会变得多么聪明和训练有素。把责任托付给他们太危险了。人工智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为核指挥和控制单独设计模块,但最终按下按钮的决定应该始终是手动动作。随着人类将战争自动化,另一种规模的网络安全将获得突出地位。
整整40年前,我曾短暂地在美国空军工作,研究一项技术,巴基斯坦空军正寻求为其新引进的f -16战斗机获得这项技术。在军事航空界,特别是在南亚,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补充。美国和以色列空军携带了一种变体,但其余的都是新-新。就在那时,通用动力公司(现在的洛克希德公司)开始宣传其针对F-16的“一弹一靶”战役。它的准确性是致命的。作为团队测试飞行能力的一部分,进行了大量的添加和改进,使其成为一个不干涉的自动瞄准系统,可以减轻飞行员的思想负担,现在可以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这和其他类似的奇特的增加了战士的能力带来了所谓的军事革命(RMA)。
后来,随着武器和平台在空中和地面的瞄准、跟踪和交战目标方面不断获得更高的保真度,杀伤力不断提高。与远程轰炸相关的类似能力是由武器实现的,这些武器在飞行中被控制时可以滑翔很长一段距离,直到它们到达最终阶段,以自主模式开始主动跟踪。直到1980年代早期,世界上最先进的空军都局限于使用中短程反辐射导弹来对付发射电磁辐射的目标——雷达的简称。1982年,以色列空军在贝卡谷地与叙利亚的短暂冲突中使用了这些武器,效果非常好。像F-16这样革命性的东西的发展和引进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思想和理论伴随着更新的思想和就业选择。随后发生的事情真正突破了门槛,引发了一场战争艺术的革命。
这就是F-16驾驶舱的运作方式:一项典型的任务是在与一群敌方战斗机和地面防御系统战斗的同时攻击地面目标。驾驶舱内脱口而出了警告、指示、目标解决方案和就业选择。飞行员手头有两项紧急任务,清理决策过程——确定优先级——并激活相关反应。它可能是在迫在眉睫的威胁下的紧急飞行机动,或激活干扰选项以破坏敌人的目标解决方案,启动自卫被动措施,并追求轰炸目标或消除空中对手的目标。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都是同时发生的行动,但关键是要把握好顺序和时机。除此之外,还需要在头脑中记住谁在哪里,朋友和敌人-情况意识-同时仍然指挥,控制和执行飞机编队的使用,以追求其目标。每个人都有宝贵的时间。可预测性可能致命。
飞行员获得的很多信息都是通过机载传感器或从编队成员和其他支援飞机那里听到的。许多年后,独立的人工智能使飞行员的工作量变得更容易,它根据预先输入的算法分解复合威胁,按优先顺序分配飞行员必须承担的任务。编队指挥官根据他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合成图像,将其他目标分配给其他成员,即使他正在进行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任务。在战斗机和支援飞机编队内以及与空中其他控制元件的即时通信和数据交换现在可以在每个驾驶舱的每个屏幕上生成合成的空中图像。飞行员分配他们的主要和次要搜索和目标区域,并通过数据交换共享彼此的信息。机载计算机已经连接了飞机系统、武器、传感器和自主激活的解决方案,减少了飞行员的工作量,使他有时间致力于最优地利用包裹中携带的全部破坏性能力。量子计算的早期模型以光速推断战斗机自己的参数,敌人的数据,并显示即时解决方案。过去的电缆和滑轮现在是通过每架飞机上的专用链路连接的数字传感器、发射器和接收器。人工智能副驾驶已经活跃了几十年。
正如在现代生活中,“物联网”(IOT)和“系统的系统”成为掌上和控制的生活方式管理系统的组成部分一样,战斗机飞行员在过去的40多年里确实生活在这些工具中。当时的流行词是“系统集成”。作为实验室的一员,创造和激活现代技术的这些过程,在当时确实是一种不太受重视的特权。随着计算速度的加快和这些计算机核心芯片的更多功能,战斗机将变得超快、超精确、超致命和超能力。战斗机将始终保持相关性,因为在人在环方程中,态势感知(SA)将是战斗中任何动态情况下最大的x因素。无人机是一种单任务机器,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完成目标,除非它在到达目标之前被吹走。就业选择将需要通过即时通信和计算将所有类型的能力交织在一起。
人工智能对战士的作用现在将超越战术发展到作战和战略。前提是训练机器模仿人类的反应。最高级别的战争决策与其说是基于既定情况,不如说是基于不断演变的战争性质。如果一台机器在长时间接触一个指挥官的决策偏好后,只学习了他的思想,它就有可能复制他的思想。但是,情况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指挥官和他们各自的思想也在变化——战争的艺术在应用和使用上可能在防御或进攻的程度上有明显的变化——这使得机器几乎不可能复制和学习到足够的行动,并在这些情况下自主决定正确的行动方针。模拟可以帮助机器学习,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所提供的东西永远无法与处于同一指挥水平的作战人员的智慧和决策艺术具有同样的可信度。
随着人类和机器在包括战争在内的大多数生活活动中融合,核武器的指挥和控制将成为阿喀琉斯之踵。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在任何程度上,都必须留给机器的突发奇想,不管这些机器最终会变得多么聪明和训练有素。把责任托付给他们太危险了。人工智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为核指挥和控制单独设计模块,但最终按下按钮的决定应该始终是手动动作。随着人类将战争自动化,另一种规模的网络安全将获得突出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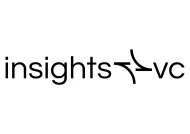












有话要说...